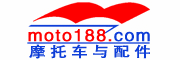在一些市民眼中,摩托車車速快、駕駛?cè)税踩庾R差,上路行駛隱患叢生;在合法摩托車駕駛?cè)搜壑校ν熊嚺帕啃∥廴旧佟⒄加玫缆访娣e少且速度快。禁摩十余年,摩托車在城市中已經(jīng)成為一種邊緣化的交通工具。即便如此,仍有大批擁躉從未停止過摩托車路權(quán)的爭取,他們的爭取不僅是簡單的呼號,也多了幾分理性的分析。
摩托車數(shù)量銳減仍有大批擁躉
國慶小長假開始的前一天下午,準(zhǔn)備從濟南回濰坊老家過節(jié)的小伙子小李打了輛出租車趕往火車站。不出意料英雄山路巨堵,本來下班就晚些的小李眼看就要錯過火車。“哥們!我趕火車,能搭你個車嗎?”坐在出租車上等信號燈時,小李看到了旁邊騎摩托車的王凱,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喊了一嗓子。王凱掀起頭盔,沖他笑笑然后指了指后座。于是,摩托車在滾滾車流中輾轉(zhuǎn)前行超車無數(shù),順利將小李按時送到火車站。
這是王凱在騎摩托車生涯中幫助打不到車、或因為堵車而趕時間的人的一個場景。王凱說,他從1998年開始騎摩托車,騎了兩年后,濟南實施交通新政,懸掛外地牌照的摩托車禁止在市區(qū)內(nèi)行駛,當(dāng)時他的摩托車懸掛的是濟陽牌照,也在禁行之列,只能放棄騎車改坐公交車。近幾年濟南城市道路越來越堵,他從2015年重新開始騎摩托車。一買了摩托車,王凱馬上考證、掛牌,自稱牌證齊全上路不心虛。
難道你走的沒有禁行路線嗎?
說到這個問題,王凱先是些許沉默,然后打開了話匣子。他說,濟南的26條禁摩路線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在我看來,禁行摩托車本來就是個悖論。”王凱說,摩托車和電動車、自行車、汽車一樣,都是市民出行剛性需求的交通工具,僅是“一刀切”地壓縮摩托車路權(quán),未免有簡單粗暴之嫌。王凱舉了個極端的例子:世界幾十個國家也包括中國,交通警察的交通工具中就包含摩托車,國家禮賓隊也有摩托車方隊。交警為何選用摩托車作為眾多基層一線民警的交通工具,這和老百姓對摩托車的需求是一樣的。
說起濟南最早始于1999年的“限摩令”,現(xiàn)在雖然不太騎摩托車卻仍然關(guān)注城市限摩的曲兵仍然記憶猶新。1999年4月,濟南市禁止對二沖程摩托車上牌。2000年1月,由于濟南市對摩托車部分“解禁”,允許環(huán)保摩托車在濟南掛牌上路。2002年10月,濟南市提出“從2003年起,市區(qū)及章丘市公安部門對二沖程摩托車不予掛牌”。同時,公安部門要進(jìn)一步調(diào)整摩托車行駛路線,限制行駛時間,盡快淘汰污染嚴(yán)重的摩托車。2004年6月,濟南市出臺地方性政府規(guī)章《濟南市機動車排氣污染防治辦法》,正式討論限摩的可行性。
今年6月底,濟南市車管所公布的機動車保有量數(shù)量顯示,濟南市機動車總保有量為1638614輛,摩托車、農(nóng)用車等其他機動車的保有量為187429輛,摩托車、農(nóng)用車占比僅為11.44%。限摩十幾年來,摩托車數(shù)量呈現(xiàn)銳減趨勢。
不少市民騎摩托車上路時,沒有懸掛號牌和戴安全頭盔,缺少必要的安全措施。 記者王鋒 攝非法上路的摩托車“帶壞”摩托車名聲
今年11月份,一則《濟南市人民政府關(guān)于加強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送審稿)》再次將“限摩”這個話題推上輿論熱點,該通告中擬將老城區(qū)和有公交車道的道路都納入摩托車禁行范圍,進(jìn)一步擴大了禁摩路線。如果完全按照該通告中涉及的路線執(zhí)行,二環(huán)內(nèi)摩托車幾乎無路可走。
“限摩的理由是什么?通告中并沒有明確給出說法。”曲兵說,該通告僅籠統(tǒng)地給出“防治機動車排氣污染,均衡交通流量”這樣模棱兩可的理由。
該通告發(fā)出后,一封長達(dá)5500余字的署名“濟南合法摩托車主李軍”的意見書發(fā)至通告所留郵箱。李軍在該意見書中寫到,所有的機動車都有排氣污染,摩托車也概莫能外。現(xiàn)階段摩托車實施的國Ⅲ排放標(biāo)準(zhǔn)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嚴(yán)格的排放標(biāo)準(zhǔn),單以個體來論,摩托車排放遠(yuǎn)遠(yuǎn)低于汽車,以最普遍的一臺125CC的摩托車為例,其油耗大約在百公里2.5L左右,而一般1.6L排量的小排量家用車平均油耗大約在百公里7L以上,哪種交通工具污染更大不言而明。至于“均衡交通流量”,李軍認(rèn)為,摩托車因其在解決市民日常交通問題方面擁有大量先天優(yōu)勢,它體積小、占地面積小、占用道路資源少、油耗少、機動靈活,對社會資源空間的利用率、城市運輸效率明顯比汽車更高。
“就算是有這些優(yōu)點,摩托車的混亂、事故多、不禮讓行人的諸多不文明駕駛行為卻是存在的。”市民張亮從未騎過摩托車,但是卻見識過諸多無牌無證的摩托車駕駛?cè)藳]有任何安全意識,造成正常行車秩序混亂,似乎是城市交通中的“另類”,因此從交通安全的角度考慮,他對這種交通工具并無多少好感。不只是張亮,認(rèn)為摩托車安全性差的市民并不在少數(shù)。
在這個質(zhì)疑上,李軍卻給出了直面問題的答案:摩托車的混亂,來自套牌、假牌、無牌、改了排氣或拆了消聲器“炸街”的。摩托車的名聲實際是被這些非法車輛敗壞的,合法上路的摩托車則因此受到了牽連。發(fā)生交通事故的,也大多是這些非法摩托車,交通管理部門需要整治的,是這些“三無”非法摩托車,而不該“一 刀切”。
“錯就錯在部分未經(jīng)學(xué)習(xí)培訓(xùn)考試的人駕駛了不合規(guī)范的摩托車,而不是錯在作為交通工具的摩托車本身。”同樣給該通告寫意見書的市民Crange的說法似乎一語中的。
城市對摩托車的包容度也該與時俱進(jìn)
即便是一名忠實的摩托車擁躉,王凱在看待摩托車問題上仍然有難得的理智和客觀。他并不否認(rèn),摩托車的最大隱患就是安全,汽車是鐵包肉,摩托車是肉包鐵,一旦出事故,容易出現(xiàn)傷亡。他去日本和臺灣時發(fā)現(xiàn),在這些摩托車行業(yè)發(fā)達(dá)的地方,所有的摩托車都懸掛牌照,所有駕駛者都戴有頭盔,在臺灣還有專門針對摩托車駕駛證考試的學(xué)校和場地。在高雄農(nóng)村,一家三口騎摩托車出行,小孩只有6歲,上車第一件事也是戴好頭盔。反觀濟南,上路摩托車不懸掛號牌的大有人在、不戴安全頭盔的更多。如果交通管理者能夠加大這些違法行為的整治力度,所有摩托車都合法上路出行,那摩托車在市民中的“口碑”也會提高很多。
曲兵告訴記者,濟南有一批哈雷摩托車愛好者,穿戴、發(fā)型都是嬉皮客,就是我們印象中的街頭“小痞子”。他們駕駛的摩托車都是1.2、1.4、1.6升排量的,和機動車排量一樣,時速上80公里是很輕松的事情,但是他們所有摩托車都有號牌,都有駕駛證,都是合法上路行駛。“要知道,摩托車也是一種文化,這和街頭極限運動、書法繪畫沒有區(qū)別。”他說。
市民Crange在其意見書中寫道,40多年前,國內(nèi)摩托車產(chǎn)業(yè)剛剛起步,技術(shù)不發(fā)達(dá),規(guī)范也不夠健全。那時,價格低廉、維護成本較低的二沖程摩托車占有主要市場,其噪音和排氣管冒出的黑煙放在今日來看,確實污染環(huán)境,有礙城市發(fā)展。但40年后的今天,摩托車無論從制造技術(shù)還是規(guī)范的完善方面都有著飛速的發(fā)展。四沖程、電噴、碟剎、靜音排氣、ABS防抱死系統(tǒng)等技術(shù)都普遍運用于摩托車,甚至安全氣囊這種曾經(jīng)只有轎車才配置的救命設(shè)備都開始為摩托車服務(wù)。因此,與時俱進(jìn)的,還要有城市對于摩托車的包容度。
車水馬龍的冬日清晨,合法摩托車車主劉利騎著摩托車行駛在明湖西路中間一排的快車道上,“法律規(guī)定摩托車走最右側(cè)一排機動車道,濟南最右側(cè)一排是右轉(zhuǎn)車道或公交車道,所以我走公交車左側(cè)的這排快車道,把自己當(dāng)成一輛汽車。”劉利說。等紅綠燈的間隙他不時地觀察,路口有十輛電動車,最多也就有三輛摩托車。這輛陪伴他七年的摩托車已經(jīng)在禁摩的尷尬中騎行了十幾萬公里,劉利盼望著有一天,城市道路上能有一條摩托車專用車道。